共计 5091 个字符,预计需要花费 13 分钟才能阅读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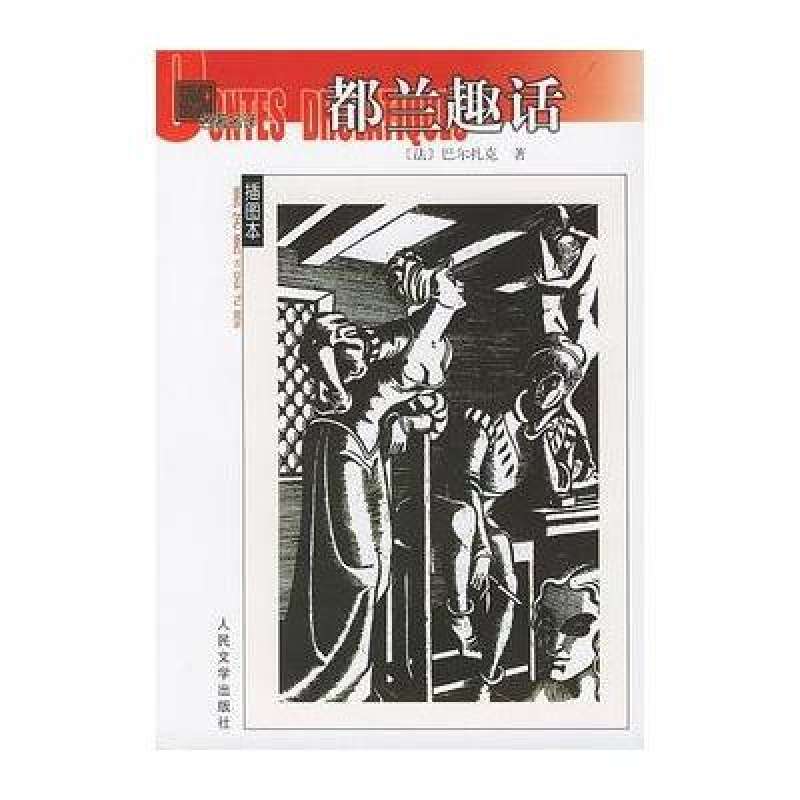
上个礼拜在图书馆(重医图书馆极小,只有1楼左边的阅览室有文艺类书籍)挑书,不经意看到一本《都兰趣话》,然后才注意到它的作者巴尔扎克。听说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据说是部很宏伟的史诗似的作品,类似于托尔斯泰老师的《战争与和平》那种,所以一直不敢下手。而这本《都兰趣话》从名字看应该是有趣的(如果它名副其实的话),很新的封面很新的内页证明这本书鲜有人问津。
坐在阅览室里,首先看到的是“译者序”,我认为,最难看的就是中国翻译家们给外国小说写的“译者序”,受大环境的影响,翻译家们喜欢在序里面介绍完书的主要内容后开始深刻批判资本主义腐朽落后的思想,并表示,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其实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言下之意,欧美的作家们全是信仰共产主义的。而《都兰趣话》的译者序无疑是我见过最好的一篇,施康强先生所写,我不认识他,但是我担保他绝对是个有趣的人,因为他把《都兰趣话》翻译得相当有趣。在译者序里,施康强先生直接摘取书中的几个故事来说明书的主要内容,看了序,再没人能抗拒这本书。
简略介绍了《国王路易十一的恶作剧》后,施康强先生立马说道:这个故事颇不雅驯,行文时涉猥亵,其余三十几个故事,十有八九也讲男欢女爱之事,但到紧要关头或一笔带过,或借助滑稽的隐喻,未堕一般淫书的恶趣。
民国时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热情提倡性教育,1926年5月张竞生出版《性史》,惹来极大争议。张竞生老师的初衷是性教育,然而此书内容尺度之开放即便是现在看来都不可思议,“各种交媾的方式,交媾前后的方法,交媾时的兴趣等……五花八门,兴情的、肉麻的、描写齐全”,这些“色情”内容令当时的大学生尤其是广东女大学生欢喜不已,据称,“书尚未到,已为各校学生定尽。计此项《性史》定购者以城北及城东某两女校学生为最多”。
特别提到张竞生老师主要是佐证施康强先生的观点,巴尔扎克尺度拿捏得当,往往于紧要关头以诙谐语带过,读来也十分有趣。
巴尔扎克故事中的时代,正是宗教影响极胜的时代,在巴尔扎克的笔下,教士们或贪婪好色、或虔诚无比,总之没有一个是中庸的,且以好色为主。修行的人迷恋尘世美色,而女人们又乐于与之交欢,这是绝妙的讽刺。故事里的女人大多是淫娃荡妇,或许这么理解不对,中西方性观念是大不一样的。故事里的国王往往是多情种子,不满足于后宫三千佳丽,喜欢出来偷腥,而一个女人又可以作为国王情人的同时又可以委身于朝中走红得宠、仪表堂堂的大臣,更惊奇的是,她非但不让她丈夫碰身子,反而使诡计让身边的侍女和自己丈夫巫山云雨,可怜的丈夫发现真相时却恼恨成疾而死(见《都兰趣话·第一卷·国王的心上人》)。
诚如序中所言,大多数故事都是男欢女爱之事,而几乎所有男欢女爱之事都可以归结为一场博弈,博弈的主角除了夫妻,当然还有第三者、第四者甚至更多特殊身份的人,如国王、红衣主教、本堂神甫。性格各异但总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共同点,故事离奇但偏取之于现实,都是日常琐事巴尔扎克却能写得妙趣横生。王小波是否受巴尔扎克影响我不知道,但是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在王小波的《青铜时代》里,他以“王二”的名义重述唐朝轶事,而巴尔扎克也声称“本书无非是一帮好心肠的老修士在开心时刻写下的故事”,“保存在都兰修道院中”,而实际上这些故事都是出自巴尔扎克之手,只是题材利用了14至16世纪的背景。不同的是,王小波用第一人称叙事,更加身临其境,而巴尔扎克跳出故事之外,作旁观状,故事性更强。
《都兰趣话》原计划写100篇,分十卷,可惜的是只出版了三卷。
最后,在隆重推荐这本书的同时,再次表达一下对本书翻译者施康强先生的敬意,施先生法文厉害,中文底子也很强,如果换作他人翻译这本《都兰趣话》,恐怕很难像这么有趣。好的翻译家,可以说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作,而施康强先生对这本书的再创作令我相当满意。在网上搜索了下,施先生的“书话系列”似乎不错,准备找个时间入手。
附文:个人史—施康强:请把我当作散文作者原文链接:http://news.163.com/05/0331/11/1G5UG4CV00011246.html用明清仿话本语言翻译巴尔扎克,把翻译作为业余爱好的翻译家

坐在中央编译局的索引柜前,施康强却更想强调自己在主业之外的身份。
在上海读中学,爱上张爱玲
人越老越怀念过去。怀旧有点像到别人家里去做客,看到的总是最好的东西。
每个人都留恋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从前未必真好,不过日后怀想起来,也觉得是好的,因为那个时候自己年轻,有很多可能性,与其说人在怀念过去,不如说他怀念过去那个充满变数的自己。
上世纪50年代我在上海读中学的时候,有机会读到沦陷时期的《杂志》和原版的张爱玲作品。在50年代的语境里,她完全是被遗忘的。我爱读她的文章(喜欢《流言》甚于收在《传奇》里的小说),是出于想了解我父母那一代人从前的生活环境的愿望。所以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心理描写,而是她笔下的40年代的上海生活场景。50年代前期的上海还多少保留一些民国余韵,可以和她的叙事参照着来看。
这个兴趣一以贯之,因此我有很“俗”的一面,就是对市井生活非常感兴趣。我在上海的弄堂里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细节让我觉得很亲切,一直都喜欢读那些记录人间百态的作品,自己也爱动手写一些这样的文章,这让我觉得兴味盎然。
从80年代到现在,我的专职工作是把中文文件翻译成外文,只是以个人身份在职务之余做点文学翻译,因此也被认为是文学翻译家,其实,心里却更喜欢别人把我当作散文作者。
现在的人可以“自我设计”,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那一代人更多是被设计的,直到80年代才能开始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是很快又到了人生将要谢幕的时候。
参与《巴尔扎克全集》,补傅雷之遗 我们这一代法国文学翻译家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也往往是一部傅雷译本。所以我们或多或少都受了傅雷的影响,但傅雷没有译完巴尔扎克的作品。
凡是念法文科班出身的人,都知道巴尔扎克是个“巨大的存在”。其实他的文体在法国并不是一流的,讲究语言的批评家觉得他的文字不纯净,泥沙俱下。他在中国的地位可能还要高于在法国。我们说他是法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法国人可能不这么想。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夏玟是我非常敬重的友人,出版《巴尔扎克全集》是她长久以来的情结。她主持出版《巴尔扎克全集》时,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律不用别的译本,而傅雷没有译过的,则另请译者。
夏玟就找了我翻译《都兰趣话》。这本书是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一个特例,和《人间喜剧》不同,这是一部《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满纸插科打诨、玩世不恭,即所谓的“拉伯雷风格”。巴尔扎克与拉伯雷一样,是都兰人。都兰人较多秉承了法国人的祖先高卢人的性格:吃东西时狼吞虎咽、爱开粗俗的玩笑乃至恶作剧。人都需要释放内心过剩的、或者是被压抑的生命力,拉伯雷的《巨人传》张扬了这种原始的生命力。巴尔扎克在拘于礼仪的上流社会厮混久了,难免也想换个活法,至少换个写法,学学他的同乡前辈拉伯雷。
嬉笑怒骂,妙译《都兰趣话》 夏玟读过我写的东西,知道我不是那种特别板着脸的学究,认为我应该能够传达《都兰趣话》那种嬉笑怒骂的泼辣风格。我读完这部作品之后,心想译本的语言风格不应该接近傅雷译的《高老头》或《幻灭》,应该也让中国读者和法国读者一样,产生一种语言上的疏离感。要在汉语资源中寻找一种对等物,我觉得明清仿话本的语言风格和它比较接近。
于是我做了尝试。读书界的反应,好像肯定的居多。但是这种做法与国内一种翻译理论是背道而驰的。有的翻译理论家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应该每二十年更新一次,使译本的语言符合接受国的当代语言。
作为一项文化工程,出版《巴尔扎克全集》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也乐赞其成。但是,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上,我认为没有必要出一个外国作家的全集。因为即便是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也不可能始终保持同一水准。
外国读者接受他更需要有个选择,一般读者只读他最优秀的作品就可以了。如果单是为了几个研究这位作家的专家学者出全集,代价未免太大。再者,真要做研究,那就必须读原文,而不是译文。
无意复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 巴尔扎克并非我最喜欢的法国作家,尽管他确实记录了整整一个法国社会。
相比而言,我更欣赏梅里美简洁的文体,更赞赏如尤瑟那尔的《哈德良回忆录》那种精练、雅致的语言。这大约是一种个人偏好,我读一部作品更多是从文字上来考量,而不是注重它的思想性或者影响力。
我对漂亮文字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喜好,读到或者写出漂亮文字会觉得很开心。但我无意复译梅里美或《哈德良回忆录》。翻译家面对那些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会担心自己笔力不够,反而对不起人家。
董桥论翻译,有个妙喻:“其实,翻译只有两种之分:好翻译和坏翻译之分。
好的翻译就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
我同意他的观点,就是说好的翻译不要强暴你的母语。中国翻译家尤其要对原作者和读者负责,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像现代中国人那样,给杰出的文学翻译家那么高的荣誉。我们既给名作家出文集、全集,也为名翻译家出版以他们的名字冠名的译文集。而在国外,译者的名字只能隐藏在扉页里,连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的故事集(法国人认为这个译本的语言胜过原作)也不例外。
社会既然如此厚爱,作为译者更应该敬业。
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有很好的传统。如果我们不妄自菲薄,可以说,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和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已经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影响了一些作家的写作风格。
80年代,参与翻译《萨特研究》“自我设计”是80年代初萨特被介绍到国内之后,才开始风行的一个说法。
1981年柳鸣九先生主编的《萨特研究》选编了他的一部分作品,我参与了翻译工作。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本比较负责地介绍萨特的书,在国内曾引起巨大的反响。
80年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不仅品种多,而且范围广泛,涉及各种流派的译著竞相问世。加上青年学生的思想比较活跃,大学生中一时出现了萨特、弗洛伊德和尼采三个热点。
90年代出版的《萨特文集》,夏玟也是主持者。到那个时候出版这套书,已经不是为了迎合时尚,而是作为一项文化工程。萨特依旧拥有相当多的读者,虽然并非人人都能理解“存在主义”的确切含义。
我感到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浮躁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80年代的风气已经喜欢拔高,攀附宏大叙事。那个时候大量引进外国思潮,实际上有很多都没有消化,只是生吞活剥。有些翻译过来的书不仅读者看不懂,我很怀疑译者自己也不一定明白。
今天,我们引进西方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差不多可以做到同步,但是质量难尽如人意。关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我曾说过“空前繁荣,泥沙俱下;高手如林,大师缺位”。学术著作的翻译同样繁荣,不过问题似乎更多。一个译者可以在几个月内译竣上百万字的作品。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假如他不是急功近利,就是译坛奇才。
口述:施康强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人物 施康强1942年出生于上海,1963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81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系毕业,文学硕士。现为中央编译局译审。译作有巴尔扎克的《都兰趣话》、《萨特文论选》、阿兰的《幸福散论》、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合译)、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合译)等。
必真好,不过来,也觉得是个时候自己年能性,与其说《都兰趣话》是施康强最著名的译作。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初新版的书封。
记者手记 摄影记者在中央编译局的楼道里巡逻一圈之后,相中了楼梯边的古旧办公柜,有许多镶着铜色小拉环的小抽屉的那种。
在电脑产生之前,前尘现世的文件就是被分类锁在这些抽屉里面,要查找起来该是多么繁琐的工作。
午时,三三两两的人群从楼梯口鱼贯而出。每当有人路过时,被我们拉到旧柜子前照相的施先生都会微微涨红脸,对人笑言:“我在作秀!我在作秀!”
有同事特意地顿首道:“的确,施先生是值得好好宣传一下。”闻及此,他迅捷地转身郑重声明:“他们来采访我,不是因为我的本职工作,而是我在业余时间做的那些文学翻译。”问他是否会因不能把兴趣当作工作而感到遗憾时,他却娓娓道出一番“职业和兴趣是可以分开的”的道理:“写文章和做文学翻译当然比较有意思,但是必须是在心情很好、有灵感的时候才能动笔。”




我还是比较喜欢法国电影。